#电子书截图
#电子书简介
引 子
这座小竹桥有年头了,扎竹的篾条已经松脱。有一处,眼看就要掉下来,不知道前面一个过桥人是什么时候过的,脚下有没有一点感觉。
这次过桥的是一个紫衣男子,走路很有样子。仔细一看,那样子在于他的身材。这种身材一般被称为“衣架”,不管什么服装穿上去都能挺拔起来。
正是这挺拔劲儿,他才走了一半,竹桥断了。或者说,篾条完全松脱。紫衣架一下子掉进水里,喝了几口泥水。
用手划拉几下,但肩上背着一个不小的包袱,划不动。只能把包袱卸掉,但刚刚走在路上时怕遇到不测,把包袱缠进了衣襟边的布扣,现在怎么解得开?
想把衣服整个儿扒掉,使了一下力,根本不可能,反而多喝了几口水。
人生真是凶吉难卜,方才还走得好好的,顷刻之间,眼看就要灭顶。自己还那么年轻,没想到死亡突然来临。没有一点先兆,没有一点预计,没有一点准备,生命如斧劈刀切,霎时断裂。紫衣架只能直着嗓子高喊救命,但心里知道,这地方冷僻极了,走了一个时辰没见到一个人。
喊总得喊,不管怎么说,总不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自己。于是,又喊,再喊。他决定,必须喊到无法再喊的那一刻。
他显然不会游泳,已经喝了好几口水,又呛着了。嘴里喊不出声音,只能拼尽全力伸手乱抓。什么也抓不住,越是用力,越是让满嘴满鼻呛成窒息。再挣扎也无用,只是放弃。放弃挣扎,放弃生命。
就在彻底绝望的最后一刻,硬邦邦的,一根竹竿捅到了肩膀。紫衣架连忙双手拉住,抬头一看,似乎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灰衫小伙子,但在慌忙挣扎中看不真切。可以肯定的是,这竹竿就是从垮掉的桥架中抽出来的。
这个灰衫小伙子,刚才怎么没有看到?只有一条路,任何一个人影都逃不过别人的眼睛,难道,他没有走在路上,只在路边的树林中穿行?
就像影子,穿灰衫的影子,在生死关头及时到达,伸下了一支竹竿,来救命。
灰影人伸到水里来的竹竿,握上去有点滑。紫衣架连忙用两手紧紧握住,用全身的力量朝岸边灰影人那里游动。灰影人也在一截截地往回收拉竹竿。
水有浮力,总算一点点到河边了,脚下已踩到河底的淤泥。但是,这淤泥是一个斜坡,脚刚踩上去,一用力,就滑了一个大踉跄。
这一踉跄,紫衣架就把所有的力气都拽在竹竿上了,居然一下子,把握着竹竿另一头的灰影人拉下了水。
“扑通”一声,是实实在在的人,不是影子。而且,灰影人在下水时也发出了一声尖尖的轻叫。
灰影人立即与紫衣架撞了个满怀。
这一撞,把紫衣架完全撞傻了。
当他猛烈地贴及了灰影人的身子,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柔软,使他浑身震颤。不只是柔软,而且是气息,不是鼻子闻得到的气息,而是一种让周围的一切都柔软的气息,串通全身。
瘦削的身材怎么会有那么惊人的柔软?他被一种从未感受过的不可思议所“点”住。
他呆立在水中,一时无思无念、无意无绪、无知无觉。
他是一个冰封了的男性板块,今天被一种陌生的力量撞出了一条裂痕。这陌生的柔软,应该来自另一种性别。
一切都还没有那么快地反应过来。等他反应过来,眼前已经不存在那个撞击体。他还站在靠岸的河里,踩着淤泥,手上握着那支竹竿。
他怀疑刚才发生的一切。难道是一个白日梦的幻觉?
上岸后低头,他发现有一道水迹拖过河边的小路,进入了树林。
他快速地顺着水迹进入树林,却又不敢往前走。粗粗细细的树枝阻拦着他,拉扯着他,嘲笑着他。
内心也在阻拦,因为再往前走,不知会遇到什么,但他能约略预感,一定会有陌生的奇异。他有自己的目的地,已经靠近,他不能因为偶遇而走神。
他这次已经整整步行了一个半月,终于到了。在路上打听过,再翻过一个山岗,就会是目的地。
目的地是两个世仇城堡,一个叫“戚门壕”,一个叫“陈家卫”,一听名字就兵气森森、战氛浓烈。他已经听说,结仇,已经二百多年。这二百多年间,发生过大小械斗三百多次。
两个家族都绝不迁徙。活着,繁衍,就是为了把地占住,与对方死拼,给祖先出一口气。
紫衣架这次来,完全是靠了从苏州去昆山半道上一位姓陈男子的指引。准备先在陈家卫找旅馆,然后等机会,经过戚门壕出海,去武运岛。
紫衣架上岸后问过路,但越是靠近越难问,路人只要一听是问戚门壕和陈家卫的事,就立即走开,低头不语。
这就麻烦了,他想,只能过一会儿翻上山岗的时候,细看眼下的布局和路途,好好猜测一下了。
他刚从河里爬起来,浑身湿透,被风一吹,有点寒意。这么热的天,怎么会产生寒意?他很快明白了,已经到了海边,吹在身上的,是海风。
自己有寒意了,立即想起了另一个人。这对他这么一个独来独往的单身汉来说,还是第一次。
另一个人,就是刚刚为了救自己也落了水的灰影人,一个突然来到又突然消失的灰影女子。她同样湿淋淋的,吹着同样的海风。
那种柔软,那种气息。当然,还有那种瞬刻之间的见义勇为。
按照世俗的说法,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没有她,就不再有自己。但是,这个对自己的生命极端重要的生命,却已经毫无痕迹。一个人,平生最要紧的存活支点并不很多,但总是抓不住。
她是过路,还是回家?回家,回哪里?是戚门壕,还是陈家卫?
第一章
1
前面所说的落水事件,发生在清代嘉庆五年,按照国际公历,也就是一八○○年,十九世纪的第一年。
说准确一点,是十九世纪第一年的夏天。
世上很多偶然小事,一探根脉却让人震惊。这个落水事件,就牵连到中国最大的文典《四库全书》、中国最大的贪官和珅、中国最大的海盗王直,跨时好几百年。这实在太让人好奇了,那就请允许我费点事,从远处说起,再慢慢绕回来。有的段落比较复杂,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明白。
先从《四库全书》说起。乾隆皇帝在晚年为了彰显“盛世修典”的气派,下令召集全国各地学者,在他眼皮底下把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全部重要文献汇编在一起。这事,最难的不是学识,而是张罗。那么多学者,名气不小,脾气很大,方言各异,举止古怪,谁能把他们拉扯在一起?那只能靠“全朝实权第一人”和珅了。
和珅对各地学者照顾得热情周到,又派出一批年轻的书吏殷勤侍候。那些书吏其实也是他的“情报人员”,帮助他更精准地掌握了汉族文人,特别是江南汉族文人的思想动态。
这天,一个书吏向他报告,徽州籍的王进士与余姚籍的徐进士一见面就争吵起来了。
“一见面就争吵?为什么?”和珅问。
书吏就把争吵的过程仔细描述了一番。
两位进士一见面,余姚的徐进士就对徽州的王进士说:“从名帖上看,贵府在歙县,是出砚台的好地方,我家几代都用歙砚。”
但是,这位徐进士把“歙”念成了“西”。这是不奇怪的,这个字本来就有两种读法,“西”的读法更通行。但在歙县的地名上,却是另一种读法。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说,别人读错自己家乡的地名是不可容忍的,他们总是高看家乡的知名度。
“我要纠正一下,我家乡歙县的歙,不读西,读麝,麝香的麝。顺便,请告诉一下你家长辈,那砚台的正确读名是什么。”王进士的语言十分犀利,除了保卫家乡的名号,还因为,自己在进士榜上的排名远远高于徐进士。
受到王进士的抢白,徐进士一下来气了。只要是中国人,最忌讳人家要教训自己家的长辈。他才思敏捷,冷笑了一下就说:“我家长辈不会忘记贵乡的地名,因为二百四十多年前贵乡有一位强人,在我们家乡留下了几笔重债。很巧,他也姓王。从此,我们那里的人怕提贵乡,把砚台的名字也另读了。”
“留下几笔重债?”王进士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说重债是客气了,是血债,而且是灭村屠城的血债,在明代嘉靖年间。”徐进士提醒王进士。
王进士立即明白过来了,说:“我知道,你在说五峰先生的事。五峰先生确实是我的本家,我们整个王家都不讳避,整个歙县都不讳避。”
“五峰先生?那是他的号,还是直呼其名,叫王直吧。整个明代,倭寇成为第一大患,而倭寇的第一首领,非贵家的这位先祖莫属了!”徐进士提高了声调。
王进士似乎早有准备,平静地说:“这事说来话长,我现在不想与你辩。只问一件事,倭寇,是日本海盗;王直,是中国徽州歙县人氏,他怎么会成为第一首领?如果他是第一首领,为什么不叫徽寇、歙寇?”
“这……”徐进士语塞了。
王进士用鼻子“哼”了一下,转身就走。
……
书吏描述完这段争吵,就不再作声,但两眼直直地看着和珅,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
和珅也直直地看着他,说:“就吵这个?明朝的事,倭寇王直,二百多年了,还有什么意思?”
书吏说:“开始我也觉得没有意思,但我后来侍候徐进士回寓所,他还在给我说王直的事。有一句话,我觉得需要向您禀报。”
“什么话?”和珅问。
“徐进士说,直到今天很多江南长者还在疑问,王直富可敌国,财产却一直没有找到。”
这一下和珅果然来了精神,问:“你是说,王直被杀后,财产不知去向?”
书吏点头:“不知去向。”
和珅不再讲话。这话题,触动了他的神经。
他十分清楚,乾隆朝经济繁荣,但由于奢靡过度,又由于自己一直在营建一个庞大的私家财富大城堡,朝廷的库帑已出了问题。乾隆皇帝并不知道财政的艰难,谁也不敢对他实言。万一乾隆皇帝察觉了什么,下令盘查,自己就会很不安全。因此,如果能用朝廷的力量追寻到王直的遗存,至少可以补充库帑。
如果追寻不到,那大笔财富就有可能落入当代强人之手。此刻,天地会秘密团体正蔓延南方,福建又兴起了由蔡牵领头的渔民、船工暴动。他们当然很需要钱,如果能够得到王直遗存,那对朝廷的威胁就更大了。和珅想,既然民间有那么多传言,即使那些强人还没有得到,也不会不听到,因此,也一定在寻找。
想到这里,和珅的眼睛亮了。
2
此后,和珅与各位学者聊天,总会频频地拐到明代的倭寇事件上。这是前朝的事,说起来不犯忌,大家都说得很直率。毕竟是学者,言之有据,思路清晰。
和珅很快就明白了,把大明王朝搅得惶惶不安的倭寇之患,最高首领确实不是日本人,而是王直。日本的海盗、浪人、流氓固然是主体,但都接受王直和其他几个徽州人如徐海、徐惟学的摆布。
王直通过贸易从葡萄牙船队那里取得了大量新式火枪,又把这些火枪卖给正处于战国时代的日本人。这使日本的军事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而他本人,也成了让日本人不得不争相追随的人物。
他是一个海盗王,更是一个国际贸易的天才。两种身份叠加在一起,当然更强悍了。他会有多少财产,人们无法估量。
和珅还知道了,王直在嘉靖三十七年中计被捕,但处置王直案件的最高官员胡宗宪也受到朝廷的弹劾和调查,因为胡宗宪牵涉到严嵩的案件。胡宗宪几年后在狱中自杀,政治角力波诡云谲,谁还想得到王直和他的财产呢?
和珅搞清了事情的基本轮廓之后,认真想了好久。他觉得追寻虽然没有把握,但数额之大让他难以抵挡,而且又挑起了他心底的某种好奇。
和珅决定,追寻王直遗存的事,必须交由自己掌控的军机处来秘密进行。他已经与军机处的两个专任官员“军机章京”商谈很久,布置了追寻计划。他反复说明了这事关及朝廷库帑、天地会和蔡牵暴动,因此全部追寻任务确实也名正言顺,是军机处的头等大事。
和珅特别关照,这件事能否查出结果,完全不得而知,因此,暂不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一向好大喜功,又被和珅历来的办事效率宠坏了,如果他知道了,就会不断查问,容不得久查无着。这一来,麻烦就大了。而且,皇帝的不断查问,又会引起朝廷各部关注,万一那笔财富与哪个系脉有涉,事情就混乱了。
于是,和珅开始安排一件平生难事:给予追查的权力,却又必须无声无息,无痕无迹。
他平日再忙,也经常会把历书和舆图翻出来,让目光在那些年号和线条间扫动。
自 序 001
空 岛
引 子 006
第一章 011
第二章 039
第三章 068
第四章 101
第五章 110
第六章 140
后 话 185
信 客
信 客 196
余秋雨主要著作选目 240
余秋雨文化大事记 242
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
——白先勇
余秋雨的有关文化研究蹈大方,出新裁。他无疑拓展了当今文学的天空,贡献巨大。这样的人才百年难得,历史将会敬重。
——贾平凹
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金庸
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锺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余光中
余秋雨先生每次到台湾演讲,都在社会上激发起新一波的人文省思。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变成了余先生诠释中华文化的读者与听众。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荣誉教授 高希均
余秋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三次来美国演讲,无论是在联合国的国际舞台,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或国会图书馆的学术舞台,都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搭建了新的桥梁。他当之无愧是引领读者泛舟世界文明长河的引路人。
——联合国中文教学组前组长 何勇
以散文风靡几代读者,早年就谙熟戏剧理论、深受现代派文学影响,更奉海明威、迪伦马特为偶像——这样的余秋雨,当他开始写小说时,会出现怎样奇异的火花?《空岛·信客》就是答案。
《空岛》的故事发生在清朝,《四库全书》编撰期间,两位进士的争吵引出一段明末海盗遗宝的秘闻,和珅随即派出黑衣人暗中追查……扬州赵府的藏书楼海叶阁,新招收的年轻秀才岑乙,迷上了昆曲名角吴可闻……海叶阁、赵府,甚至整个扬州城,都悄然卷入一场被巨大力量操控的风波……赵府的巨额财源来自何处?来无影去无踪的吴可闻真实身份是什么?赵府老少如何逃出军机处的罗网?悬疑、推理、武侠、历史、美学,看余秋雨如何将这些元素编织成电影感十足的故事!
《信客》的背景是鸦片战争之后沿海城市崛起,男人去城里打工,女人在农村守着老小,两边需要牵线,于是有了“信客”。信客由乡人担任,凭信任维系,他们肩上挑的不仅仅是书信、货品,更是家家户户的死生祸福。可是,当“信任”却被一条小小的红缎带意外改变,牵线人的步履应该何去何从?平凡人的渺小付出,如何勾连起更大时空的生存依据?余秋雨用典雅朴素的文字勾画出两位信客的命运,又将淡淡的哀伤和对人生的信心蕴藏其中,读来让人回味、深思。
自 序
一
在我的小说、剧作选集前面,要抄录一段自己的文章——
一个人心底的文化潜藏,往往与他的日常工作有很大不同。
我的基本身份,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学者,平日又习惯于用行书和草书记述阅读心得,创作古体诗词,难道,心底还有别样潜藏?
果然如此。
我在内心无法割舍的,是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从贝克特、尤奈斯库、萨特,到卡夫卡、奥尼尔。对我自己的创作影响最大的,是海明威和迪伦马特。
此事说来话长。
我本来早已对很多以往的世界名著产生厌倦,没想到现代派文学干脆利落地把它们全然搁置,只探寻人类整体的生态悖论。这一来,文学一下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高度,却又与普天下每个人有关,这实在让我心旷神怡、百脉俱开。
但是,这么大的人类课题,如何才能表现在一部部作品中?那就只能依靠寓言式的象征了。因此,所谓现代派文学,也就是一个“象征的森林”。
这个“象征的森林”深幽无比,然而对一般读者来说,障碍太多,雾霾太重,容易晕厥,容易迷路,因此时间一长,人们也就不太愿意进入了。现代派渐渐由热闹走向寂寥、分化、式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海明威和迪伦马特。他们克服了那些同行的毛病,讲述故事津津有味,描写古今生动有趣,乍一看很像写实主义作家,但稍加体味就能发现字里行间另有宏大意涵,仍然指向人类整体的生存悖论。这就是“不像象征的象征意义”、“很像历史纪实的历史嘲讽主义”。
我的创作,受他们的影响较深。
二
在《冰河》初次出版时,我写了这样一则“题记”——
我让一个象征结构披上了通俗情节的外套。而且,随手取用了中国古代的衣料。
斯特林堡(J.A.Strindberg)说,好作品是成人的童话,因此未必要有凶杀和毒药。成人为什么还要有童话?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回答道,为了唤醒复生的奇妙。
在《空岛》初次出版时,我又写了一则“题记”——
我用历史纪实的笔调,写了一部悬疑推理小说。但是,聪明的读者很快就看出来了,纪实和悬疑都不是目的,而是指向着一个“意义的彼岸”。那彼岸,有关一种美丽的生命哲学,尽管这种美丽总是会毁灭或遗失。
也有可能找回,那就必须用艺术,而且是象征的艺术。
这两则“题记”,大体已说明我的创作追求。
从作品看,我的“现代派”非常东方。本来“现代派”是不受地域限制的,我在《布莱希特之后》一文中曾经列举西方现代派大师们对于东方美学的深深痴迷。我是东方人,在这方面自然就更加当仁不让了。
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广大读者和观众,是否接受这种创作追求?
要验证,最敏感、最尖锐、最无情的地方,莫过于剧场。那就必须以《冰河》为例了。
《冰河》和它的前身《秋千架》、《长河》曾经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和上海大剧院演出,皆称盛一时,创造了票房纪录。更惊人的是在台北“国家剧院”,演出时正逢“大选”,剧院外的广场天天有几十万人参加“选举造势”。海内外没有一个剧团敢于在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演出,因为每一个观众要看戏就必须披荆斩棘地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才能到达剧场大门,太艰难了。但是,奇迹般地,我妻子马兰还是坚持在那里主演这部戏,居然天天爆满,而且延续了很长时间。
在那些难忘的夜晚,我一次次在剧场的门厅里长时间站立,一边看着场内座无虚席,一边看着场外人潮汹涌,充分感受到一个戏剧创作者的满足。同时我也明白,我们的艺术追求达到了。
不管是古典象征主义,还是悬疑象征主义,我只企盼把人类整体的生存悖论引向彼岸净土的诗化境界。这本是一种幻想,没想到居然有那么多观众和读者热情趋近,并诚意投入。我把这件事看得很重,甚至把它看成“此生不枉入世一遭”的证据。
二○一九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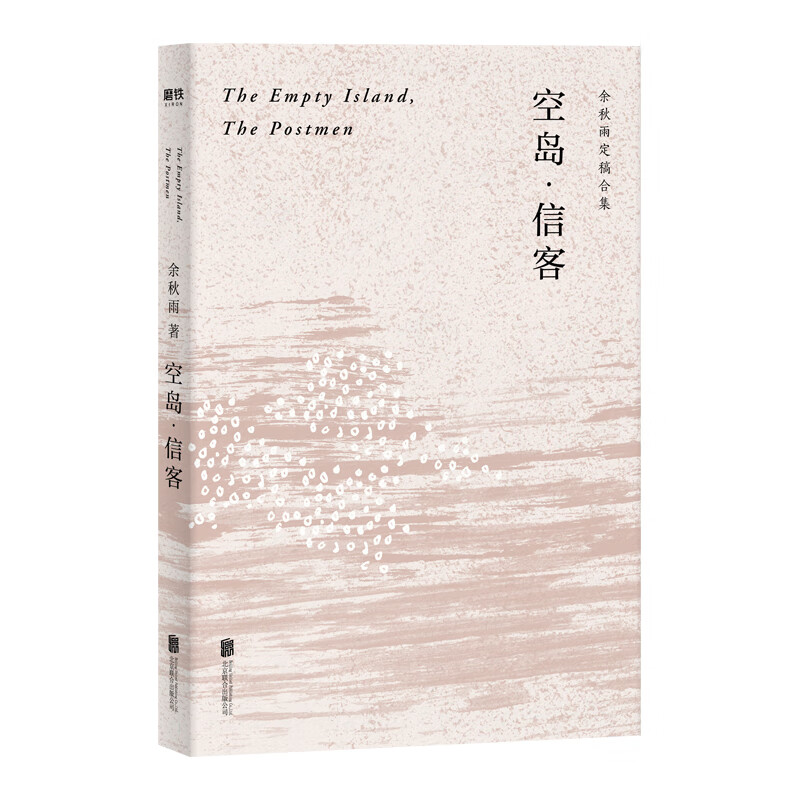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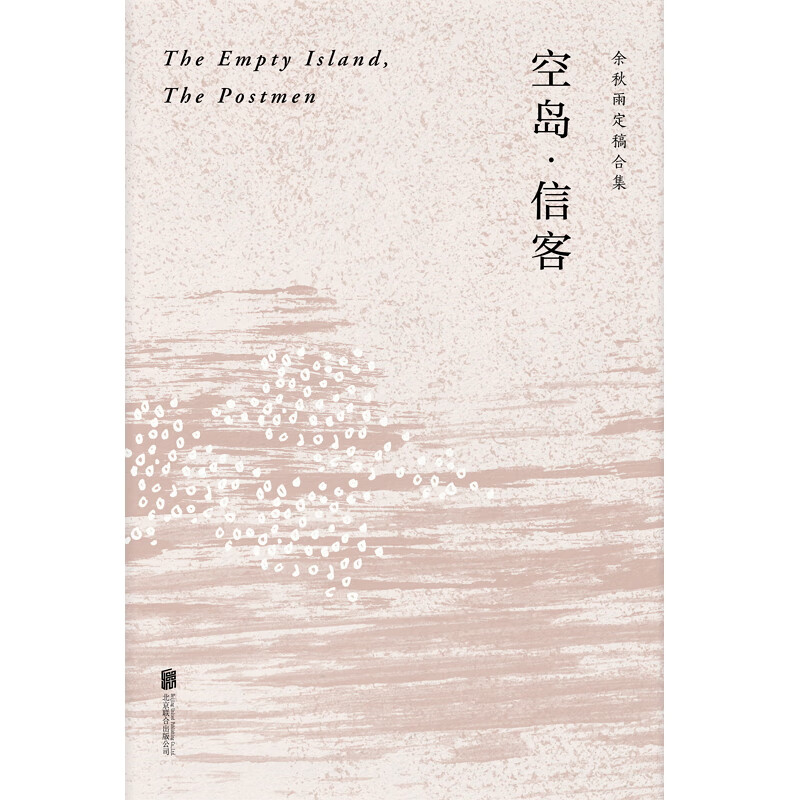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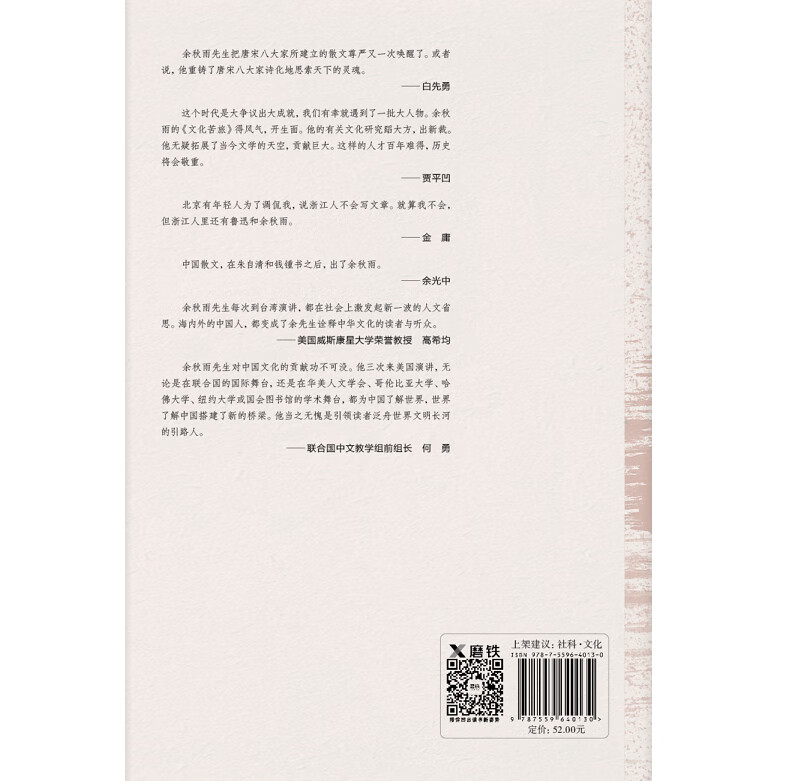








评论列表(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