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截图
#电子书简介
译者语/ l
陈 弘 绪题词/ 9
李 明 睿题词/ 12
陈 婥 题词/ 15
高 世泰题词/ 18
白话 影梅庵忆语 …… l
冒襄 传/ 49
亡妾董氏小 宛哀辞并序 /52
冒姬董小 宛传/ 66
文言影梅庵忆语 …… 75
冒襄 年 谱/133
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才是宇宙间之至美。
——林语堂
捧读本书,汉人内心曾经拥有的那块温玉以及那由内而外的阵阵清风,几近拂面而来。
——倪泰一
本书是冒襄关于爱与离散的泪笔记人之书,共四卷,一记作者与董小宛相识、相爱,终成眷属的曲折过程;二记焚香品茗、花前月下的妩媚时光;三记甲申之变后流离失所经历的险难困苦;四记与姻缘相应的谶言和梦兆,全书哀感惋艳,琐细真挚,却也春光无限。
作者冒襄,明末清初文学家,年少时即被董其昌(明末清初大书画家)称赞“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其人风流而有气节,明亡后不仕。《影梅庵忆语》为冒襄的传世之作,首开忆语体先河,追述了他与董小宛的相识相知相爱,是对明清易代文人群体追求自由精神的一种反映,也是个体生命在困厄世道中写下的浪漫诗章。“忆”是文序之魂,更如杜茶村所言,是两个生命之间的“宛然对语”。
2020今注全译插图本,由著名诗人、作家龚静染译注,译文通俗流畅且保留了古典文学行文美感。
锦瑟书系,精装典藏。古典雅趣的装帧设计,让作者的原文意蕴得到艺术化呈现。
《影梅庵忆语》是明未清初的大才子冒襄为亡妾董小宛写的一篇长文。冒襄( 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一号朴庵,又号朴巢,江苏如皋入。他出身仕宦之家,“少年负盛气,才特高,尤能倾动人" (《清史稿》)。董其昌曾将他比作初唐的王勃,期望他“点缀盛明—代诗文之景运”。但冒襄—生怀才不遇,六次参加乡试均落第,仅两次中副榜。郁郁不得志之余,他与张明弼结盟,积极参加复社,主持清议,有经世雄心,同陈贞慧、方密之、侯方域一起被称为“四公子”。但时乖运蹇,“会乱作,遂不出”,冒襄只能以清流自居,过着以著述为乐的隐逸生活。
明末清初,历史大潮剧烈翻涌,朝代更迭,兵戈四起,甲申之变、南阴兴亡、清兵南下等接踵而至。虽在乱世,但当时的江南却是一派艳靡的景象,秦淮河畔樽酒交错,琴瑟箫笛依旧,夜夜笙歌不辍,而复社文人成为了其间的主角。当时的风流才子与秦准名伎,如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孽与顾横波、吴梅村与卞玉京、侯方域与李香君、王稚登与马湘兰等,成就了一时之盛。阴未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数百年一遇的大时代,世道人心也处于最为复杂的时期,忠将、贼子、遗民、贰臣同处一朝,上到皇帝大臣,下到文人墨客,都被江南的绝代佳粉连接在一起,演绎了一段段风流佳话,可谓是旷世少有。冒襄也不例外,他与“秦淮八艳”之一的萤小宛从相识到相爱,最后走到一起。他们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可以说,《影梅庵忆语》就是明清易代文人群体追求自由精神的一种反映,也是个体生命在困厄世道中写下的浪漫诗章。
《影梅庵忆语》虽然是一篇回忆性文章,但因其长达万言,以足够的篇幅细致入微地讲述了故事的诸多细节。其中既有对乱世之中人物命运的描写,也有对日常生活中各种情趣的漫叙,还有对男女之间真挚情感的回忆,甚至还勾连出了大时代中那些几乎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隐秘往事。所以,《影梅庵忆语》不仅具有文学性,同时也具有历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在文学方面,《影梅庵忆语》首开“忆语体“ 文学的先河。它是杂揉了传记文学、笔记体文学和明清小品文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这种抒情性自传文体对后世文学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近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性。自从《影梅庵忆语》刊行后,《香腕楼忆语》《秋灯琐亿》《浮生六记》《眉珠庵忆语》《倦云忆语》《寄心琐语》《昭明忆语 》等“忆语体”文学作品纷纷问世,成为了一道道文坛风景,这可能是冒襄没有想到的。但细细解析这些文本的叙事结构和风格,确有其独特之处:才子佳人的今世奇缘、战乱中的家国忧思、温婉纯真的女性情怀、痛彻心扉的生死追问,都在诗性的演化中为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受,而这正是它风靡一时的原因。所以,“忆语体”是明清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它对清早期性灵文学的影响也是有迹可循的。
在历史价值方面,《影梅庵忆语》虽是写个人的生活经历,但其中涉及了不少史实,如记录了1645年6月冒襄举家逃往浙江盐官过程中的遭遇。冒家一大家子辗转数月,颠沛流离,当时在马鞍山“遇大兵,杀掠奇惨”,“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遗矣”,而这完全可以作为明清战乱历史研究的个案。又如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传说,事关“秦淮八艳”之一的陈圆圆。据传,吴三桂引清入关就发生在陈圆圆与冒襄的一段情缘之后,而这也在《影梅庵忆语》中有所印证,其中勾连的一段大历史,非稗官野史史所能比拟。当年陈圆圆情定冒襄,两情相悦,但这是一段隐秘的历史,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以“陈姬”代替陈圆圆,其实是有时事之讳的。他第一次见到陈圆圆时对她印象极佳,可谓惊艳:“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 陈圆圆见到冒襄后也是一见钟情,发誓跟随他,定下“终身可托者,无出君右"的决心,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为窦霍门下客以势逼去"。这段史实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假如冒襄提前十天接走陈圆圆,那就没有后来的董小宛,更没有了吴三桂为红颜而改变历史路径的粗莽之举。而冒襄当时的"怅惘无极”也就具有了天地间的大悲悯,不单单只为一个女子,我相信此处必有一种历史的无情和虚无。
《 影梅庵忆语》精彩之处,在于通篇叙述命运沉浮,一波三折,有荡气回肠之感。但它又不仅仅是有小说般的曲折情节,其过人之处,在于文字用情至深,从中也正可以看到冒襄复杂的思想转化过程。冒襄毕竟是官宦世家子弟,董小宛则是秦淮伎女,无论最初冒襄是如何贪恋董小宛的美色,在选择纳她为妾时,他仍然十分犹豫。但董小宛不顾重重阻拦与危险追随冒襄,表现出惊人的决断与跳出藩篱的决心,这才打动了他。但进了冒家门的董小宛地位仍然是很低的,“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婢妇有加无已”“当大寒暑,折胶砾金时,必拱立座隅”。确实,董小宛是绝顶聪明之人,
她把自己当成家中的婢妇,这样才能赢得众人的喜欢。她经历过秦楼楚馆的逢场作戏,却对三从四德的传统思想牢牢遵循。特别是在冒家举家逃难之时,董小宛对冒襄说:“当大难时,首急老母,次急荆人、儿子、幼弟为是。彼即颠连不及,死深菁中无憾也。”虽然其话语中有大义靡然,有对冒家的感恩戴德,但实则也是她对自己地位低下的自知之明。
其实, 冒襄是在日常生活中才真正认识和爱上堇小宛的。冒襄经历了为父请命和自己六赴乡试落榜的种种辛劳, 早已厌倦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将董小宛娶回如皋之后,乱世遗民的隐逸之志弥坚。在《影梅庵忆语》中,他用了大篇幅来描写董小宛的“情趣”和“慧心”,如在女红织绣、花草种植、品茗烹调等上,都展现了她极高的品味和审美情调。董小宛也是个才女,在帮助冒襄编《全唐诗》时,又顺便为自己编了一本《奋艳》,书中内容涉及“服食器具、亭台歌舞、针神才澡,下及禽鱼鸟兽",连冒襄都称赞其“瑰异精秘"。所以,冒襄在与董小宛一起生活的那些年中是非常享受的。红袖添香,缠绵徘恻,这在乱世之中实在是一段难得的温馨而静谧的岁月。难怪冒襄在董小宛去世后长叹:“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冒襄文字中人性的温度,他参透生死,心无尘碍, 坦然将董小宛放到了一个美丽、善良、性灵的自由境界中,塑造出了一个鲜活动入的文学形象。
我们还应该看到,《 影梅庵忆语》也是一篇关于明清时期艺术与生活的长文,文笔精湛,活色生香,它真正的文学价值也许就在于对士大夫生活和趣味的细腻描绘上。
《影梅庵忆语》在感伤的底色下是对一个仙侣大梦的追悼,江南、佳人、名士是梦中的场景,奇花异茗、玉臂云贵皆是过眼云烟,红颜薄命的悲剧命运中传递出的却是阴柔、优雅 、颓废的气息,虽有灿烂,实为悲苦,而这或许正是人们深深迷恋它的原因。
也正因为此,围绕《影梅庵忆语》的话题经久不息,甚至还多有人对其进行杜撰和附会,比如说董小宛并没有死, 而是被抢到宫中,成为了清世祖的董鄂妃,生造出了一段后传。更有甚者,还论证《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顺冶,而林黛玉就是董妃,证据是:“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小宛是苏州人,黛玉也是苏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王亦在扬州。小宛来自盐官,黛玉来自巡盐御史之署……” (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但胡适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就批驳了这种“无稽的附会”:“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倍,断无入宫邀宠之理。”当然,这样的无中生有尽管多是对历史的膛想,但毕竟《红楼梦》到底写的是“秦淮残梦忆繁华”,或许《影梅庵忆语》中正有着与之相通的气息,所以也使其具有了广泛的影响力和经久的艺术魅力。
《影梅庵忆语》写于冒襄四十岁时,“余年已四十,须眉如戟”,应该是董小宛新丧不久所作,即顺冶八年( 1651) 后。文章甫出,即刻印寄给他的朋友赏读,如陈弘绪,“今年春,雉皋冒子辟疆驰新刻数种,见寄中一秩,题《影梅庵忆语》”;又如陈婥,“岁甲午,余归自北,遇辟疆……手《影梅庵》见示”。从中也可以看出《影梅庵忆语》刻印的时间在“甲午”,即顺冶十一年(1654)之前。在现今留存的本子中,引用最多的则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如皋冒
氏丛书》本,系“冒氏第二十世族孙”冒广生汇辑而成。冒广生是光绪时期的举人,与林琴南、刘申叔一起被誉为“近代古文三大家”,对其乃祖冒襄非常崇拜,收集编有冒襄诗文作品集,所以他对《影梅庵忆语》的考订较详,版本也较为完备可信。本书主要采用的就是冒广生《如皋冒氏丛书》本,并在此基础上整理了冒襄年谱。
值得一提的是《影梅庵忆语》的结尾部分,虽是作者亲身经历,却犹如神来之笔,也是对“忆语”的一种呼应。冒襄写到痛失董小宛之前的一段恍惚经历:他去问卜,得一 “忆”字,后半生将以忆为生。当然这个字也成全了《影梅庵忆语》这篇名文的传世。“忆”是文序之魂,更如杜茶村所言,是两个生命之间的“宛然对语”。
龚静染
2019年9月1O日 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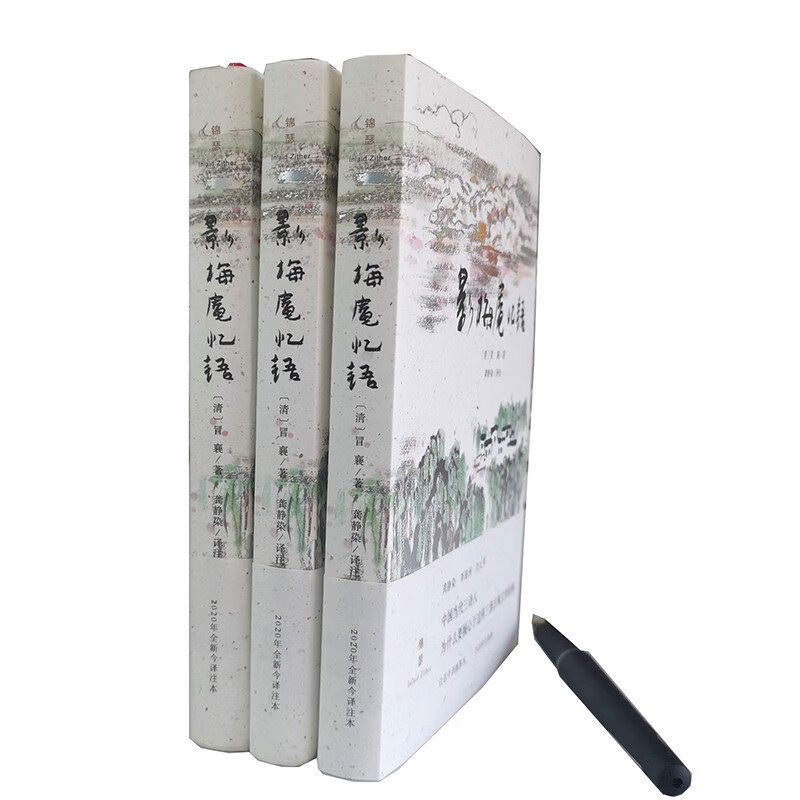








评论列表(0)